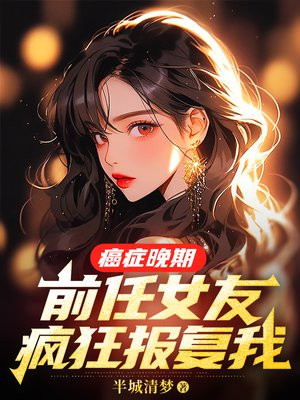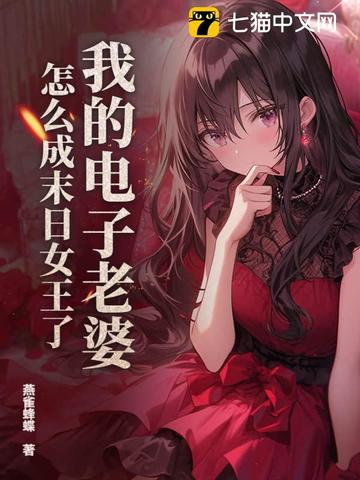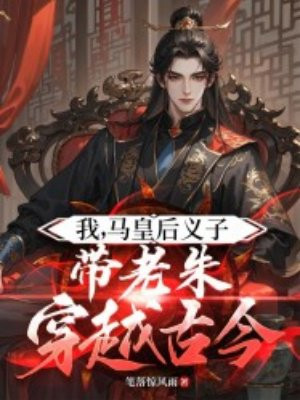首发:~大虞篇之西征
徐承借由三州党被大肆弹劾之事,强行将政事堂九相压得抬不起头,按照他的意思开始改造现有的官制。
但是这套官制自大华起,已经沿用千年,所产生的轨迹已经决定了世间万事的走向和规律,贸然打破就犹如强行破坏世间法则一般,引起的动荡不是徐承凭借开国之威就可以压得住的。
所以徐承也没敢完全推翻旧制,只是在旧制的基础上做了一番改良和增加。
第一,取消政事堂。增加设立内阁,内阁官员设置三名主官,称为阅章大臣,正二品。下设十名副职,称作执笔大臣,从三品。再往下则设立三十名从四品的执笔郎作为内阁的基本班底。凡是奏章全由执笔郎进行归类和做出处理意见,接着再呈交执笔大臣做出意见,最后才到阅章大臣进行批复。这一做法就是把原来的政事堂九相分解为四十三人,同时这四十三人的权力相比九相又差得远了,直接解除了相权的威胁,但又保留相位的基本作用。
徐承的意思其实就是将内阁等同于皇帝的助理,协助皇帝处理政务,批阅奏章,也就是说全天下但凡能放到徐承案几上地奏章都要先经过内阁过滤一遍才能来到徐承的案几上,毕竟徐承每日需要批复的奏章实在太多,他早就暗中叫苦连天了。同时内阁并没有决断之权,只有奏报和驳回的权利,凡是到了内阁的奏章,需要通过或者需要徐承亲自过目的才会被挑选出来送到徐承的案头,反之,则由内阁直接驳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内阁官员不再像政事堂一样,除了大相之外,大部分都兼着一部主官之职,这内阁官员就只能是内阁官员,不得兼职,且被徐承列为永例,后世君王亦不得打破。
但是,为了避免出现挟私报复或者一些官场上的龌龊事,凡是驳回的奏章皆需要最少两位阅章大臣联名签字同意驳回,并且注明原由。而不同意驳回的阅章大臣也要签字注明不予驳回的原因。若是连续驳回超过三次则第四次必须直接通过审核,送到皇帝跟前由皇帝决断,当然若是皇帝也觉得驳回有理,坚持上奏者会则会被降级处分,若是皇帝觉得驳回无理,内阁处理过这份奏章的官员也会遭到降级处分,若是事关重大则看事态严重再行处理。
同时,内阁作为真正的天子近臣,也不是谁都能进的,也不是进去之后就能做什么官的。
就说这阅章大臣,要么出任过六部尚书或御史台和四方镇军将军这样的一部主官或一方主将之人,要么从执笔大臣升迁,要么皇帝钦点,不然不能出任阅章大臣。
而执笔大臣同样是要么出任过六部尚书或御史台和四方镇军将军这样的一部主官或一方主将之人,要么从执笔郎升迁,要么皇帝钦点,不然不能出任执笔大臣。
而执笔郎则是宽松一些,但是也要求出任者最少做过一部副职,例如侍郎、中丞这样的官职,要么吏部考核连续三年以上得优的五品以上官员,还有就依然是靠皇帝钦点。
这样的班底取代政事堂,一来等于完全分解了相权和将权,同时看似尊贵,可都没有什么实权,既不能分管各部,也不能做皇帝的主,大大地消除了朝堂之上出现权臣的可能性。
第二,保留六部这个最核心的架构,但是取消民部,民部所负责之事交由其他五部将贴近自己的事由接受,改设立工部,负责制造器械、建筑、修桥补路等事宜,最起码将兵器铠甲等相关兵事的制造这一事宜从兵部剥离出来,因为兵部若是掌握太多兵事大权,一旦被人掌控则很容易威胁皇权,尤其十黑水油这种徐承发现的神兵利器,更不能给兵部一起掌握,所以必须从跟兵部剥离出来。除了这些,六部一切运转仍按旧制来走,就是奏章不再直接呈交皇帝,而是呈交至内阁,由内阁来决定是驳回还是上交皇帝阅览。
第三,保留御史台,同时增设监察院,隶属御史台统属,但检察院主官也就是监察大夫虽是御史台主官御史大夫的副手,但品秩却和御史大夫相同,同为正四品。
而监察院的作用就是将御史台的作用发挥到更大,从前御史更多是巡视天下,闻风而奏,但这样效率低了些,且容易生出胡乱攀咬之嫌疑,所系徐承决定直接设立监察院监视天下,朝廷各部以及天下各州各郡各县乃至军中均要安排监察院的人,按照级别划分分别为负责京都朝廷的则称作监察令,负责州郡的则称作监察使,负责军中的则称作监察司马。
这些监察院的官员不吏从任何驻点的部门管理,直接向监察大夫汇报。但同样的,这些监察官员在任何地方也仅有监督之职,并无干预之权,一旦发生有监察院干预地方政事或军事者,斩立决!
这样,徐承可以说是从上到下都把所有官员都监控的死死的,说是监控,其实就是在控制这些人犯错,希望监察院的出现能让这些人收敛一些,明白自己的用心良苦。
第四,取消州府,撤销刺史等相关职务,将天下重新划分为十道,每道唤做道政院,设立一名主官,称为行台,品秩为三品。行台下设副职二人,唤作台令。再往下设置十二名正副台使,分别对应原先的六曹。
看似道政院跟原来的州府没什么区别,其实完全不一样,首先道政院行台看似品秩比刺史高了两级,辖下之郡比原来的州府还多,可权力却小得多了。道政院的职责跟御史很像,有巡视各郡的职责,但又跟御史有所区别,御史只是负责纠察奏报,不得干预地方政事。而行台则有直接干预政事的权力,跟内阁有些相似,就是凡是各郡所提的政令奏表等借由道政院整理审阅,一应流程和职责和内阁一样,区别就是内阁对应的是全天下,而道政院对应的一道之郡。既无刺史的决断大权,又有刺史的干预监察之权。
同样的若是下面郡城上交至道政院的提案或汇报都必须经由驻郡监察使联名签字,因为监察使虽无干预之权,却有知情之权,一旦被驳回超过三次,驻郡监察使则会直接上报监察院,由检察院联合内阁及关联事宜的部门联合派人处理。
第五,就是徐承最在意地一点,就是兵制的改革,且主要是针对州军,因为都军和镇军基本都是独立在政治体系外,只效忠天子,稍加约束一般不会出现什么大事。可是州军就不一样,跟地方关系错综复杂,很容易就混成一块,形成割据。所以徐承想要改变这个情况就要从根子上解决这个事情。
徐承的思路是这样,原来驻州驻郡的的军队皆是由州郡负责供养,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朝廷的负担,这些不负担不单单是钱粮上的,还有运输上的,这是一项利政,所以徐承并不打算改变它。但是若要驻郡脱离跟州郡的关联又不可能,说得难听点,州郡可是财神爷,驻军吃喝拉撒都得靠着这些州郡刺史和太守的供给,难免就要时常打交道,一来二往的就有了交情,一旦有了交情就难免容易结党营私,若只是中饱私囊倒还好,就怕发展下去还会出现霍乱天下的事情。
所以徐承决定依照取消州府的办法取消州军制,改为郡兵制。同样依瓢画葫芦但又区别于政治划分的道政院将天下重新划分为十八路,每路唤作军机堂,设立一名主将,称为主帅,品秩等同于行台,正三品。下设副将二人两名副帅,两名司马,四名参军。再往下就是驻郡守备营统领。统领再往下就是校尉。统领驻郡、校尉驻县。统领与校尉数量跟一路军机堂主帅辖下郡县数量一致。军机堂不设军团,仅有三千军机堂路兵护卫,实际的兵马皆在各个统领手上,军机堂并无节制之权,但有监管职责。
军机堂谓之各郡县兵马的作用其实跟道政院对各郡县官员的作用一样,更像一个中转站,作为各郡县和朝廷乃至天子之间的言路。同时军机堂的路和道政院的道所划分的区域还不一样,各有各的划分执法,很容易出现一路军机堂所辖制之地同时落在两个乃至三个甚至四个道政院所辖的局部郡县,反之道政院的辖区也可能同时驻守几路军机堂驻郡,这样一来,起码在很大程度消除了高品秩文武之间的勾连,将这种可能出现的风险控制在郡县一级,哪怕真的出现问题,以郡县一级的实力,想要颠覆天下简直是痴人说梦,再徐承看来,既然不能完全消除隐患,就将风险降低到最小。
第六,既然州军有所调整,四方边军也不能不动,四方军的编制依旧不变,只是专门针对四方军专门从户部、兵部、工部专门设立了一个边军制置处,独立于六部之外,但是对边军拥有升迁调派、粮草器械拨运的作用,凡是边军将领升迁调派、器械损毁或更换皆由边军的镇军将军将通过边军制置处协调完成,可以说边军制置处就是边军的顶头上司,而不是兵部,同时边军制置处对边军仅有统属之权,但却不能调动边军兵马,边军兵马仅能镇军将军可以调动,但调动之前须通过监察使司马盖上监察分处的印信至边军制置处分处方可调兵,且四个边军驻军处皆设有边军制置处分处,哪怕事出紧急亦不会出现来不及调兵遣将的情况。
第七,取消都军雪虎军番号,统一称之为禁军,外军则称为左、右禁军,中军则称为亲军。但是进入禁军者皆赐九品出身,入亲军者皆赐八品出身。但禁军选拔制度有变,不再单纯的以京师户籍为主世家子弟出身者选拔禁军士兵和将领,而是各军有军功者皆可入选,或是通过禁军设置的考核亦皆可入选,就跟天下文人科举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样一来最大程度上保证禁军乃天下最为优秀的精锐之一,又打破了京师子弟垄断进入禁军的优势,也让天下当兵的有个盼头。
同时禁军的士兵也不是优秀就可以永远待在禁军不走,一旦到了校尉这个级别,但凡有所升迁,就只能外放至边军或者路军区历练,后期但凡立功或再有升迁,会视情况决定是否再次调回禁军。而禁军的统领级别的将官,从今以后,若非特别优秀者,一般都由边军和路军准备升迁的统领中进行选拔。
第八,朝廷不再设立上柱国、大将军这样的军职,这些职务的作用跟丞相一样皆由内阁代替皇帝负责。
第九,为预防一个人在位置上久了,会产生隐形的势力,徐承决定,凡是出任主官者,除去升迁罢官和死在任上的,无论品秩高低,八年至十五年一换。例如一部尚书,最高不得在任十五年,若是十五年内无法更进一步,进入内阁者,要么就更换至别的部门,要么就地告老。而品秩越往下,时间越短,层层递进,最高十五年,最低八年。而且不单单文臣,武将亦是如此。且五品以上,不得原地调动或升迁,不管是平级还是升级调动都必须调离原有任职属地或部门,属地针对地方,部门针对朝中。
第十,地方上,凡是大虞官、将,三代内不得同道为官或同路为将,若是一文一武,若是所在地官道和将路有所重叠,品秩较低者调至别处。而朝中,亦是三代内不得同在一个部门。总体来说,凡是大虞官、将三代出仕者内不允许在职权上面有任何交集。
这些就基本是徐承改制地框架,地方上的倒还好办,原本的刺史、都督这些封疆大吏皆提升为一道行台和一路主帅,虽说权力变小了,但是品秩却实实在在提升了两级,江上这两年南征北战,许多有功之人都不知道如何封赏,朝廷增加出来的一些部门和职务正好可以中和调动一番,也大致将这些人都安置完了。
可难就难在原来的政事堂九相,这些人除了原本的大相石腾,和大宗正徐建,其他的七相皆是兼着六部和御史台的主官的,若是让这些人都入了内阁,看似荣耀无比,可实际上权力可是大大的缩水了,若是不进内阁,他们地位上虽不能说一落千丈,但也是无法跟往日相比,难免会有落差和怨气。若是因此跟他们弄得离心离德反而不美,毕竟他们都是能力俗、功劳不小的忠臣,徐承不能亏待这些人。除此之外,世人皆知,他们都是徐承的心腹重臣,若是亏待了,谁还为徐承卖命。
于是徐承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在太庙旁边起了一个名臣楼,将政事堂九相和其他有大功的功臣都派了数百名巧工能匠,用上好的木料将这些人的样貌做成木雕,摆放其中,每具木雕身后还竖立一块巨大的木牌,上面记录着这些功臣的生平事迹,以及对大虞的功劳,以供后世帝王瞻仰。
且还颁布了旨意,能以木雕之身进入名臣楼者,死后皆陪葬皇陵,配享太庙,受大虞世代香火。且非皇室者,死后皆以国公追赠。若生前已是国公,死后则以郡王追赠。皇室宗亲者亦是如此,但若生前已是亲王爵位,其子袭爵则不降级,依旧为亲王。
这就是无上的荣耀,不过要等死后才得,但这些待遇足以保证这些人身后家族长盛不衰,毕竟人家老祖宗坐在太庙中享受皇家香火呢,谁敢欺负?这也算是大大弥补了削减这些人权力或地位的补偿,想来这样,这帮人怕是不会有那么多意见了吧。
徐承这一举动,确实把原本怨气深重的几位大佬安抚了下来,可不生气归不生气,可是事情还是要解决,这些人是进入内阁还是留在原来的位置,一时间不管是徐承还是这帮子人都犯起了难。
于是徐承就跟原政事堂八相一共九人在御书房中大眼瞪小眼,不知如何是好,徐承更是耐不住性子直接摊牌道:“诸位,事已至此,总归要有个结果,大家伙拿个章程出来吧。”
石腾本来就没有出任部门主官,他自然就是进入内阁接受三大阅章大臣其中一个位置,而且儿子石斌也争气,不到二十的年纪就已经成为正四品禁军中军将军,乃天子亲卫头头,前途无量,就算自己现在告老都没有压力,可自己也不过四十出头的年纪,怕是离告老还远着呢。
所以相对其他人他可是轻松的很,于是捋了捋胡须道:“陛下,以臣之间,此间我等八人和远在建邺的大宗正,无论如何,最后怕是都要进入内阁的,只是进入的时间早晚罢了。如今臣并不在六部或其他部门任职,所以自然可以直接进入内阁,而大宗正如今还须坐镇南京,不宜回朝,所以臣以为先不要考虑大宗正。而剩下之人臣是这么觉得的,凡是有替代者皆入阁,无替代者则保留。”
吴绅随即苦笑道:“现在怕是下面的人都急着要咱们腾位子呢,又怎么会没有人接替?现在的大虞别的不敢说,人才一抓一大把,比户部里面的存银还多。现在不是有没有人解题的问题,是该如何接替的问题,难不成六部和御史台主官全都抽空充斥内阁?一下子这么大变动,我担心会出问题。”
徐虎也点点头道:“吴相所言有理,臣亦认为,不宜动作过大,该徐徐替换,毕竟都是朝廷中枢部门,牵连甚多,动作太大确实不妥。”
吴绅随即笑着对徐虎道:“怎的还叫我吴相,如今已经没有政事堂了,哪来的相公?”
徐虎随即笑道:“这不是都叫习惯了,一下子改不了口,再说了不叫吴相该怎么叫?还是直接称呼你为国丈?”
吴绅无奈道:“叫什么都行,就是莫要带个相字就行,你若是喜欢,直呼老夫姓名也不是不行。”
徐虎忙笑道:“国丈说笑了,我岂敢直呼你的姓名。”
徐承随即摆摆手道:“好了好了,这称呼之事我给你们定,内阁没有组起来之前,一切还按照政事堂的官职称呼。现在莫要跑题,说说该怎么推动此事。国丈你刚才已经说了一半,接着说说你的想法,其他人等国丈说完再行插嘴。”
徐虎被徐承一顿不轻不重地斥责,不由得尴尬地吐了吐舌头,不再言语。
吴绅见徐承已经点名,也赶忙应道:“是,陛下。老臣以为既然石相不兼主官,可先行入阁,臣手下两位侍郎其实早就具备主持一部的能力,只是臣挡在前面,他们没法升迁,只能苦熬,如今户部这边,臣也可以脱离,直接进入内阁,同时臣手底下的两位侍郎可择一人也进入内阁,兵部那边,大部分皆是皇室宗亲,且人才济济,想来徐相亦是不难脱离,且兵部因为皇室宗亲众多的关系,想来会是六部之中动荡最小甚至没有动荡的部门。而吏部尚书本是大宗正出任,大宗正出任不久后又因陛下要攻伐渝州而兼任了建邺留守,至今未卸下这个重任,基本吏部之事皆是由原本出任刑部侍郎而调任至吏部出任吏部侍郎的徐方在主理,后陛下登基,大宗正才得以卸下吏部尚书之职,将徐方扶正,接掌吏部。但徐方执掌吏部时日尚浅,纵算是将吏部管理得有条不絮,但臣认为徐尚书还是需要继续磨炼,毕竟年轻,往后入内阁并不是难事。六部之中户部、兵部、吏部最为重要,分别执掌着天下钱粮赋税、将帅兵马、全国官吏,是朝廷根基中的主梁,如今户部、兵部皆能安然交替,所以吏部尚需平稳过渡,所以臣认为徐尚书还是不懂为好,徐尚书以为如何?”
年仅三十出头的徐方,留着一撇短髭,长相倒是一般,但胜在气质威严正气,见吴绅点到他,也不紧张,大大方方地抱拳道:“吴相所言,正是我心中所想,就是吴相不提,我也会向陛下提出,目前吏部确实还需要我坐镇。”
徐承亦是点头认同道:“国丈所言有理。”
吴绅继续说道:“礼部尚书邱相所在礼部可以抽身。刑部麦相和民部尚书王相的情况跟吏部尚书徐相一样,也是接管不久,亦不宜现在就入阁。何况民部改成工部,一切相应事宜和人员变动更大,也不宜此时变换主官。而御史台的乔相则更不能动,因为新增监察院,御史台整个权力架构因此受到变化,必须乔相亲自坐镇,待监察院之事有了成果,方能抽身而出。粗略算下来,如今政事堂九相可入阁者仅四人,远远达不到内阁所定的人数,若只是执笔郎倒还好办,可这阅章大臣和执笔大臣拢共就有一十三人,如今才有石相、我、徐相、邱相四人,还差九人,我属下的户部侍郎罗明亦可入阁,也就是无人,还差八人,当如何是好?”
徐承略微沉吟道:“这样,朕也给你尔等凑几个人,一个是镇东将军徐康、驻守飞鸟的征西大都督符啸、河北安抚使王松、河北招讨大都督徐汇,加上这四人,拢共九人,其余四位则从原本的州刺史和驻州都督以及各部侍郎中择优选择,这内阁班子也就算搭起来了,至于执笔郎也是从诸多五品官员中择优选择,但真有一个要求,这些执笔郎必须要有外放的履历,朕可不想选一些不知民间疾苦的书包子。事出从权,这内阁初建,百事待兴,先就这么定了,往后内阁选拔就要按照朝廷的制度来走。”
众人见徐承已经发话,当即齐齐施礼道:“谨遵陛下旨意!”
徐承也是松了一口气,终于将此事推动了一大步,可是这些新的制却不是一日两日便可实现的,这是需要以年来计算的时间成本去调整,比如人员的调配,单单这一项就够吏部把屁股都忙到冒烟。但是内阁一旦组建起来,其他的事情就可以按部就班的推行,徐承有信心最多两年的时间,就可以让大虞的官制焕然一新,再用两年的时间加强国力,五年内西征统一天下,而那时的徐承也不过才二十三岁,这样的年纪和这样的功绩,到时在史书上的记载,徐承相信除了千古一帝四个字,别的字眼都不够资格来形容自己这耀眼的功绩。
想到此处,徐承也不由得暗暗得意,心情一好,就想找人分享,于是徐承当即就朝凤仪殿走去,此时他迫不及待找个人陪他说说话,随便说点什么都可以,刚好听说吴叶最近有些不舒服,自己最近因为改制大计之事又太忙,根本没空关心吴叶,刚好今日开了个好头,也空闲了一些,自然要去看看吴叶。
此时的徐承可以说是心似飞箭,没多久就来到了凤仪殿,门口的宫女远远见了徐承的仪驾,赶忙入内通报。吴叶则在飞雪四人的搀扶下慢悠悠地走出殿外,站着在殿门边等着徐承出现。
徐承一出现在凤仪殿的大院就笑哈哈得高声说道:“皇后免礼吧,赶快让飞雪她们给朕泡些花茶,朕有些渴了。”
吴叶当即吩咐飞雪和梅霜进殿泡茶,自己则领着晚冬和冰儿待徐承走近了才盈盈下拜,施了一礼道:“臣妾见过陛下!”
徐承笑呵呵上前握着吴叶的手道:“哎呀,真不是说了,皇后免礼了嘛,你怎的还给朕施礼。”